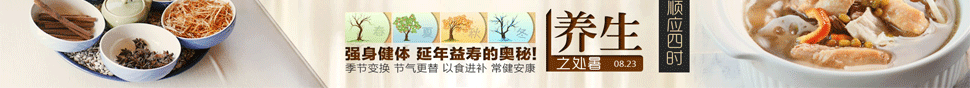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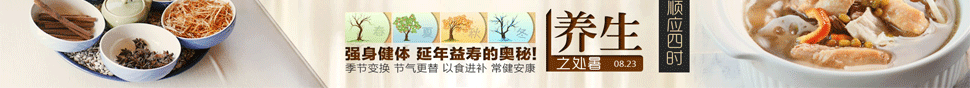
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5月1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0年前,在文章发表3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当年文章的作者、编辑和定稿者,听他们讲述文章创作前后的故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引发大讨论
当年作者、编辑和定稿者揭秘创作前后
记者 周继坚
原载《法制晚报》年5月
胡福明文章作者,写作文章时为南京大学政治系副主任、助教。此后曾历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务,年退休 王强华文章编辑之一,修改文章时为《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后曾担任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务,现为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 孙长江文章最后修改执笔者和定稿者,时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后曾担任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现已退休
4月的南京已是绿树葱茏,当本报记者如约来到北京西路江苏省政协办公室内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在伏案看报——他正是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
这位年前从江苏省政协第一副主席任上退休的老者,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看报。30年前,在构思那一篇后来轰动全国的文章时,不会骑自行车的胡福明还只是一个大学助教,每天得医院的妻子送饭。 南京邂逅记者约来历史性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后来轰动全国的文章,竟然源于30年前南京大学助教胡福明与《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的一次邂逅,之前两人并不认识。
今年75岁,现任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的王强华还清楚地记得,年5月,时为《光明日报》记者、哲学组组长的他到南京出差,采访南京地区理论界的一次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揭批“四人帮”。
正是在这次多人参加的会议上,王强华认识了作者胡福明。 观点提出研讨会上遭众人“批斗”
在这次会议上,胡福明的发言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他提出,“文革”中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胡福明说,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强调生产力是第一位的,不能够批判。
然而这一发言在当时几乎是孤立的,几位与会人员发言反对,他们转而批评胡福明的观点。
“原本是批‘四人帮’的,却变成批胡福明了,但是我内心赞同胡的观点。”王强华说,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人只好宣布休会。休会间隙,王强华便通过别人介绍和胡福明认识。
会后,王强华向胡福明提出邀请,要他给《光明日报》写点文章。
“当时只是约稿,并没有确定题目。”时隔30年,两位老人仍然能清楚记得南京邂逅的一幕。 被批“黑帮”助教遭到学生抄家
在胡福明的印象中,早在王强华约稿以前,他已经开始构思写一篇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
当时的南京大学成为“文革”的重灾区,校长匡亚明遭到错误的批斗,还是助教的胡福明也曾被批为“匡亚明黑帮”,不仅挨了批斗,还被学生抄了家。
“大概是年,‘两个凡是’的提出令我感到惊讶。”胡福明原本以为,“四人帮”被抓起来后局面会有转折,但是2月7日“两个凡是”的提出,让这种期待落空了。对此“很不理解”的胡福明开始酝酿写一篇文章来批判“两个凡是”。
时隔30年,胡福明对记者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两个凡是”,则不会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也可能不会有这么一篇文章。
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在南京大学给哲学系学生讲课
顶住风险一个人“秘密”写作
胡福明将文章的主题指向“两个凡是”,认为这是拨乱反正的主要绊脚石。他认为,当时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
“年年搞阶级斗争,年年搞运动,能受得了吗?”胡福明坚持写文章的缘由,是因为觉得这样下去只会祸国殃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必须拿起自己的笔,写点文章。
“‘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就应该否定!”回忆当年的书生意气,胡福明依然慷慨激昂,这也成为他写文章的动力。
胡福明在写稿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身边的任何人,就连妻子也只知道他在写文章,但“并不知道写什么文章,给哪里写”。胡福明担心,一旦出事会让身边的人受到牵连,“我也知道有风险,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医院走廊熬夜写出文章提纲
胡福明记得,文章的思路在年6月份已经基本确定,但是写哲学文章并不似散文或者小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胡福明四处搜集材料。
然而就在胡福明草拟提纲的时候,他的妻子忽然被查出患有肿瘤,医院做手术。
6月的南京已经非常炎热,一个病房住了四个女同志,晚上不太方便,医院的走廊里看书写作。医院的走廊灯光昏暗,由于经济困难,胡福明连手电筒都买不起,好在40来岁的年纪,视力还算不错。
走廊里只有几把简单的椅子,最恼人的还是蚊子的侵扰。胡福明坐在椅子上,一边用蒲扇驱赶着蚊子和炎热,一边仔细地查阅资料。
看书入神的时候,“嗡嗡”的蚊子总能趁胡福明不备偷袭成功。但胡福明仍然坚持看书,“一天要带四五本书看”。
等到写提纲时,走廊里没有桌子,胡福明就只好蹲在地上,趴在椅子上写。有时候太晚了,他就趴在椅子背上小睡一会儿。这样坚持了一个星期,妻子出院时,胡福明也完成了文章的提纲。
毛泽东手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一稿标题没出现“唯一”
经过三轮修改,胡福明的文章在年8月份写成,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时他想起了《光明日报》王强华的约稿,便将稿件寄往北京。
此时文章标题中还没有“唯一”二字,但胡福明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共产党宣言》)的态度证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们看作一次完成的真理,而是始终用实践去检验……这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四个论点文章巧打“语录战”
胡福明最初的提纲提出了四个观点,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以代替批判‘两个凡是’”。
为了减少阻力,胡福明也打起了“语录战”,大量引用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原话,举的例子也来自马列主义著作。“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要反驳的时候,必须先驳倒这些语录。”胡福明说。
“当然,这也是一种保险的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胡福明也知道,直接反对“两个凡是”是不现实的。
初看文章编辑没打算刊用
文章作者胡福明年9月从南京寄出稿件,这期间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在外出差,12月下旬才看到胡福明的文章。
王强华现在清楚地记得,胡福明当时寄来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报社的编辑一开始并未打算刊用,“感觉理论性太强”。
王强华看到后,觉得是篇好稿子,“虽然很理论化,但触及了当前的现实。”
当时的王强华,深感“两个凡是”的禁锢,使得一些学术理论探讨无法展开。因为他不相信学习语录可以“立竿见影”,因此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正是有了这种经历,让他对胡福明的文章产生了共鸣。
王强华决定,这篇稿子在哲学版刊发,于是给胡福明去了两封信,希望他尽快修改。
年1月,胡福明收到《光明日报》的回信。
书信频传提醒作者把握分寸
记者看到了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当年给胡福明的第一封信,信中提出:“稿子需要精练一点,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在分寸上宜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的感觉。”
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中,王强华多次将清样寄给南京的胡福明。
三十年后,记者有幸在胡福明家中看到了这两份清样:纸张已泛黄,边缘因风化严重已经出现缺损。胡福明仔细为清样铺上纱丝,再用油纸包了两层,这些年来他视若珍宝,从未轻易示人。
“你看看,文章主要的观点,都有粗体字标注。”如今白发苍苍的胡福明,读出那些久远的文字,仍然声音激昂。 慧眼识才总编要求放在头版
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这篇文章要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需要做进一步修改。当时,文章作者胡福明恰好要来京出席全国哲学讨论会。
年4月13日,胡福明一到北京,就被请到杨西光的办公室对文章进行商讨,其中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孙长江。
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家中一个没有封皮的小笔记本记下了三十年前那次商讨的纪要:总编辑杨西光提出,文章的要害应该是揭批“两个凡是”。
胡福明也对那次商讨印象深刻,当时杨西光拿着一份清样说:“这篇文章原本要在哲学版刊出的,我看过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杨西光还提出,文章要加强战斗力,内容可以更展开一点。要仔细推敲,不要被别人抓住“小辫子”。
反复斟酌“两个凡是”字眼被代替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文章作者胡福明和编辑也曾有不同的意见。当时《光明日报》有编辑提出要点名批评“两个凡是”,但是胡福明不赞成,认为这是一个策略不够的做法。
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至今保存着一份从原稿抄下来的摘要,内容是《光明日报》的编辑对文章作的修改:“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作者胡福明说,因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看了后也觉得直接点出来不合适,感觉太露骨,接下来,文章被修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理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用“一切”和“所有”替代了两个“凡是”的字眼。
所见略同中央党校亦写同题文章
年4月13日,第一次商讨胡福明的文章时,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邀请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来参加也是“有目的”的。杨西光曾在中央党校学习,得知中央党校也在酝酿写一篇类似的文章。
孙长江回忆说,中央党校在胡耀邦的领导下,理论研究的氛围非常浓厚。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主持创办的《理论动态》每五天一期,每期一篇文章。
年春,中央党校学员在讨论研究路线斗争史时,觉得“两个原则”(即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有点不大清楚。孙长江觉得,“两个原则”很容易误解为“两个标准”,主动提出就此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
孙长江介绍,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说,列宁好像有一句话,叫做“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于是,当时文章的题目被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孙长江就开始写文章的草稿。
孙长江与吴江
巧妙联合文章经胡耀邦审定刊发
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记得,经过作者胡福明和《光明日报》反复修改后,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于年4月23日和24日先后两次送到中央党校,由他和吴江修改。
孙长江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该稿为基础,结合党校的文章草稿进行了修改。
孙长江说,为了赶进度,他还采用了剪贴的形式,将决定保留的《光明日报》稿原文用剪刀剪下来,直接贴在修改稿件上。
孙长江在最后一段的修改中,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他还精心给文章加上了小标题。
孙长江和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在年4月27日修改完毕后,胡耀邦同志年5月6日审定了这篇文章,由孙长江拿到中央党校印刷厂付印,10日在《理论动态》发表后,次日在《光明日报》刊登。
王强华说,文章十易其稿,前六稿均为胡福明修改,第七、八稿为他和《光明日报》等人修改,第九稿为中央党校理论组组长孙长江修改,第十稿则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
冒险发表文章曾遭遇领导批评
经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
次日,《光明日报》用头版半个版和第二版半个版的规模,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从来都是《人民日报》发稿,《光明日报》转载,但这次不一样。”时任《光明日报》编辑,现任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的王强华对记者说,“大家都认为这是篇好文章,但当时它的发表确实是有风险的,还曾遭遇领导批评。” 总编力挺文章冒风险也要发表
年,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曾提前告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文章将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在《光明日报》上刊登。
时任杨西光秘书、现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陶铠曾在《杨西光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一文中写道:“曾有人提醒,发表这篇文章要冒很大风险。他(杨西光)说,‘我已经老了,‘文革’那么大的险滩都闯过了,还怕什么呢?’”
陶铠还写道:“文章发表前,他(杨西光)在一次报社负责人会议上宣布要发表这篇文章,说‘这是一篇事关中国命运的文章。如果结果好,那不用说;如果我们因此受到误解,甚至是受到组织处理,由我来承担责任,但我们要相信,历史最终会公正地作出结论。”
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的该文
规避风险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为什么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王强华记得当时有好几种说法:
一种说是“卸包袱”,有人说总编辑杨西光弄了一篇大文章不敢用,有什么风险可由《理论动态》承担,因为这份刊物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定才能发表。杨西光听说后很生气,他说:“谁说我们不敢用?就写上‘《光明日报》社供稿’。”后来,《理论动态》刊发时就署上了这么一行字。
第二种说法是寻求支持和扩大影响。杨西光曾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领导沟通,希望他们能转载。而过去都是《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稿件,还没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载《光明日报》稿件的先例。
王强华更倾向于“互相支持”的说法。“《光明日报》有好文章,之所以《理论动态》可先发,是因为它是内部刊物,当时发行量只有几百份,而《光明日报》当时的发行量是几十万份。”他说。
5月11日《光明日报》
文章发表很多人表示支持作者
年5月11日早,正在南京家中的作者胡福明打开收音机,广播里传来:“《光明日报》今天刊发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文章发表了!”胡福明一下子兴奋起来,前后写作修改了一年时间,终于发表了。《人民日报》理论部一位副主任还写信过来,要求他继续写文章批评“两个凡是”。
当时胡福明所在南京大学的很多老师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学校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令他感到放心。刚“平反”恢复职务的校长匡亚明也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很好嘛。” 轩然大波有领导批评是“砍旗”
很快,作者胡福明接到北京朋友传来的小道消息,说中央有领导批评这篇文章是在“砍旗”,这个消息并不让胡福明感到意外。
“越是在上层,可能感觉这个问题越严重。”当时作为编辑的王强华也隐约感觉到一些压力,但他觉得“文革”已经过去,应该不会有什么上纲上线的大问题,最坏的打算顶多是在《光明日报》干不下去了。
“文章发表一两天后,我估计是出事了,因为总编辑杨西光一直阴沉着脸,不说话。”王强华说。
小平讲话 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巨大的压力下,当时《光明日报》内部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砍旗”了,文章闯大祸了;一种则坚持这是好文章,发表是一件好事。
年6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科技和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来个思想大解放。
6月到11月,真理标准大讨论从中央到地方开始蓬勃地展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光有文章,没有人发动这个讨论,文章实际上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在王强华看来,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偶然性,是邓小平发现了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领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就记录了邓小平的这样一句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是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 文章命运讨论带来思想大解放
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没有解放思想,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在王强华看来,不是文章改变了命运,而是邓小平领导的大讨论改变了中国命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当时已经提出,邓小平领导的大讨论更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王强华表示,大讨论带来人民头脑的解放,思想从本本主义、个人崇拜等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
“任何人随便讲一句话就是真理,就要执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王强华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摘录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真理标准”时间检索
年5月,《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向胡福明约稿
年9月,胡福明将已修改三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寄往《光明日报》
年4月10日,原本计划在哲学版刊发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被《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发现,决定改在《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
年4月27日,中央党校孙长江和吴江对文章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并定稿
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
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向全国转发
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胡福明谈十九大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致敬:年代
胡耀邦主导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刘崇文:胡耀邦的最后半年
王彦君:马文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赵树凯:九号院与中国农村改革
不应忘却的年巴山轮会议
戴煌: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柳红:还原年代被遮蔽的历史
王岐山和改革四君子的故事
蔡晓鹏:九号院·杜润生·中央一号文件
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陈锡文:我与中国农村50年
翁永曦忆杜润生:“守住底线,敢讲真话”
朱嘉明:程秀生与"中心"故人点滴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功之臣
徐雪寒:虽九死而无悔
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
习仲勋主政南粤,力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小平南巡:告别革命转换经济模式
周其仁: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
詹国枢:胡耀邦为啥左右为难
成曾樾:年胡耀邦激赞个体户
詹国枢:我为什么佩服万里
孟晓苏:我给万里当秘书的日子
林毅夫:朗润园里的孔夫子
刘鹤:"非常重要"的中国经济掌门人
改革老将徐景安为中国再出发指点"路标"
何维凌侧写:他有一颗动荡不羁的灵魂
帮着"摸石头"的人——回忆张少杰
肖玉环:告别白南生
周其仁:纪念杨小凯
郭凡生:追寻我们共同的理想
朱学勤忆杨小凯:有一件事我抱憾终生
杨小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
肖玉环:长歌当哭送君远行
送别新三届学友曹征海
汪丁丁:看不到中国社会中精英所起的正面作用
皇甫平:突围利益藩篱思想须再解放
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
黄晓京:物非而人是——旧信札的记忆
牛文文:袁庚、王石与蛇口基因
年取消反革命罪的第一声
谭启泰:风,吹灭了蜡烛,吹旺了篝火
钟健夫:年代政治激情与《南风窗》
徐建:中国缺的是德高望重的大律师
吴思:思想的创造力
雷颐:精神启蒙远未完成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haitongpi.com/tpzz/1143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