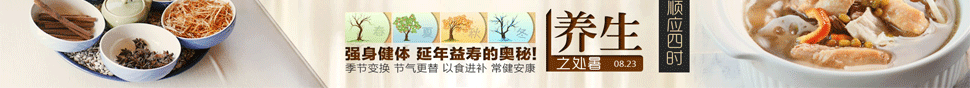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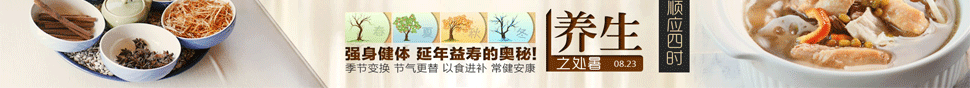
周末看历史
年的1月2日早晨,正是北京城滴水成冰的季节。老皇帝已经在前一年10月8日龙驭宾天,紫禁城里的新主子换成了宝亲王弘历。勤劳的店主们早早开了店门,迎接南来北往的客人。突然,街口传来了低沉的锣声,马蹄撞击路面的得得声,还有逻卒驱赶行人的叱骂声。
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传来声音的地方,只见一队身披号衣,手持长矛的清兵走来。前面四人举着回避字样的招牌,后面是两辆开顶的牛车,车中各反绑着一名犯人,脖颈后面还插着一块两尺来长的木牌,前面一个写着“钦决逆犯曾静”,后面一个写着“钦决逆犯张熙”,两人的名字已用朱笔勾划。牛车的后面又是一队清兵,中间拥着一乘四人抬暖轿,暖轿中坐着今天的监斩官、刑部尚书杭奕禄。
“当初听说他们鼓动岳钟琪造反,心里还佩服是个血性汉子,谁想案发后却成了丧家之犬,到处乞求饶命,后来竟恬不知耻地到处现身说法,天地间还有如此不要脸的人”……
牛车上的曾静紧闭双目,面如死灰,众人的骂声清晰地传来。他知道自己当反面教员6年多来,早已是臭不可闻的狗屎堆,既不容于百姓,更不容于士林,已为天下人所不耻,今天的结局也是解脱。生命即将走到终点,8年前的那一幕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诱供
年(雍正六年)9月26日上午,古城西安,刚从外面访客回来的川陕总督岳钟琪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一位自称张倬的书生突然从人群中跃出,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策反信,信封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署名为“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信里对当今皇上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攻击,列举了“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的十大罪状,说雍正继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并对雍正的继位正统提出了严重质疑;信中还说华夷之防断不可开,满人不配统治汉人。希望岳大人作为岳飞的后人,继承祖上遗志,利用手握重兵的机会,成就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
岳钟琪是岳飞21世孙,出身武将世家,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战功卓著。年羹尧飞扬跋扈被整肃,岳钟琪接任了他的川陕总督位置。位高权重的川陕总督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特别是他岳飞后裔的独特身份。民间传播着岳大人和朝廷不和的传闻,这些传闻一致认为:岳大人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起兵造反。
岳钟琪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同时对这个自称张倬的投书人严加审讯。那书生只说自己名叫张倬,这书信乃是他的老师夏靓所写,其他的只紧咬牙关,一概推说不知。岳钟琪投鼠忌器,怕万一把人打死了,那可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说,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岳钟琪和陕西巡抚西琳临时搭档,一起来审这个案子。随后的审讯中,岳钟琪主审,西琳则躲在屏风后面听审。冷眼默对的张倬依旧一言不发。被众衙役又是一顿狠揍。但这次手下留情,虽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却未伤筋骨。
当夜,张倬被人从监牢中悄悄提出,早已等候多时的岳钟琪一改白天的模样,摒退左右,松开捆索,握着张倬的手惭愧地说:岳某早有反清大志,奈何时机尚未成熟,只能隐忍不发。对壮士用刑,除了掩人耳目,还有是为了试探壮士的真实身份。
见张倬不为所动,岳钟琪命人送上酒菜,邀他边喝边谈。席间,岳钟琪连连向张倬敬酒,大骂满清鞑子和走狗,亡国之痛溢于言表。又诉说自己乃忠良之后,实在是愧对先人。说到激昂处忍不住涕泪交加。张倬感动之余,话多了起来,便谈起反清大计,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岳钟琪当下约张倬明日一起盟誓结义,共举反清大旗。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张倬接到一个密室,密室里香炉也已摆好。见张倬进来,岳钟琪二话没说,便拉他一起焚香跪拜,两人结为兄弟。岳钟琪还对天发誓说,从此后两人同心同德,患难与共,驱除满人鞑子,倘有二心,一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义结金兰打消了张倬仅有的一丝疑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读书人,哪知道官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种诡计,很快将整个事情和盘托出。
公知
原来,张倬的真名叫张熙,是奉他老师曾静——也就是策反信上那个化名夏靓的人之命,前来投书的。
曾静是湖南郴州永兴的乡村塾师,原先是个秀才,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以授徒为生。曾静家里没钱,学生也很穷,加上个性偏激,就像今天的愤青,对社会甚有不平之气。这时,他遇到了精神导师吕留良。
吕留良是理学家、江南大儒,嘉兴桐乡人,已去世40余年。早年吕留良也是顺民,考取过功名,后来结识黄宗羲等著名公知后,开始壮怀激烈起来。晚年为了拒绝博学鸿词科的推荐,宁愿削发为僧。吕留良天资过人又勤奋好学,诗文时评出版俱是一把好手。
虽然他拒绝了仕途的诱惑,后来还因为政见不同,与黄宗羲绝交。但这些都关系不大,重要的是他已经把自己变成名公知,社会美誉度高企。特别是他选评的时文,抓住了当时科举考试的主旋律,成为“程法”和“定义”,风靡一时。
这一切都是在统治者的眼皮底下进行,从来也没有人去告发。这一方面可见清朝入关已80余年,两个舆论场的对立依旧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吕留良做事隐蔽,那些观点大多托孔子之名,只有少数有心人能够体会深意。但因此付诸行动的,也只有曾静这个特例。
就在策反岳钟琪前一年,曾静派张熙到吕留良家求书,小儿子吕毅中把父亲留下的“反动至极”的诗文都给了他。曾静沉溺其间难以自拔,全盘接受了吕留良“华夷之别”的排满主张和继续革命的理论。结合自己从路边社打探来的最新时事动态——大多是夺嫡失败后,允禩、允禟等人的太监、奴仆在流放途中散播的,理论联系实际地认为岳钟琪是岳飞之后,想必身在曹营心在汉,就精心鼓捣了这份书信前去策反,想成就一番千古事业。
当年5月,张熙变卖了仅剩的一点房产,和堂叔张勘经贵州赴四川,到四川后却听说岳钟琪已经调任陕西。两人又前往西安。一路晓行暮宿,吃尽了苦头,终于在9月13日赶到了西安。正当他俩准备前去投书时,却听当地人说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臣,那些君臣隔阂的传言纯属胡编乱造。张勘听后心里害怕,一个人跑回了老家。张熙也想打退堂鼓,但又想自己倾家荡产才来一趟,不能就这样前功尽弃,于是就有了之前的一幕。
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身边没有诸葛亮这样的谋士。张熙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定能担此重任。岳钟琪让张熙告知曾静的住址,好派人前去迎接。不知是计的张熙供出了所有信息。演完戏的岳钟琪脸色一变,喝令将张熙押监,并通知兄弟省市相关部门迅速捉拿曾静。
曾静被捕后,雍正先后派副都统海兰及刑部侍郎杭奕禄前往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进行审问,不久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又根据两人口供,令浙江总督李卫严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
证据表明,曾静案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会激起雍正的冲天怒火,等待他们的将是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可现实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奇书
曾静在长沙和北京受审时,生活上受到破格优待,杭奕禄等他百般开导,最后雍正竟然还将与岳钟琪及各省封疆大吏、各部尚书关于此案的数百件奏折、谕旨等大批绝密文件,让曾静跪读。
一看风向有变,庆幸自己有可能捡回一条命的曾静,立马从愤青转身为五毛,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的反清活动“直与禽兽无异,狗彘不如”,表示追悔莫及,对之前仰慕不已的吕留良恶毒攻击。
庭审记录更像是一篇悔过书,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讯官按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这个称职的反面教员,每次在稍做解释之后,立马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反证他散布的谣言是如何地荒诞不经。最后还捣鼓出一篇“归仁说”,总结自己的最新思想成果。
审讯过程中,雍正发出一系列谕旨,公开为自己继承皇位和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进行多方面的辩解,宣扬自己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及80余年统治期间的伟大成就。以期唱想主旋律,并在庭审记录前加了长长的按语。
有关材料包括上谕10道,审讯词和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后附曾静“归仁说”汇编成册,全书4卷约10万字,定名《大义觉迷录》。这是一部封建社会由最高领导人钦定发行且内容绝无仅有的奇书。只是千篇一律如同新闻通稿,明显透着作秀的成分。
《大义觉迷录》。
年(雍正八年)春,《大义觉迷录》刊行后立即发往全国各个府州县,要求当地每个读书人和乡野小民都要知晓。更有个别地区逢初一十五有专人进行宣讲。同时还特别规定,每个学宫都备一册,学子们必须人人观览知悉。无疑,知识分子是此书的目标阅读人群。
同时,雍正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观风整俗使是个非常设机构,职责是巡察地方、劝谕化导风俗,相当于今天的舆情监控室兼纠风办。
按逆向思维的方式来推理,一地设立这样的衙门,肯定是舆情斗争非常激烈。事实确实如此。就在前两年,浙江接连发生汪景棋、查嗣庭两起文字狱,两人的诗文中发现攻击康熙、讽刺时事等重大不法行为。两人被查的主因是背后的大老虎倒台,一位是年羹尧的秘书,一位与隆科多交好。年、隆两人被打翻在地后,他们也很快受到牵连。
加上之前浙江当地士绅议论时局的风气很盛,包揽诉讼、抗欠钱粮等方面也都不是省油的灯,雍正心里嫌恶已久,借汪、查文字案对浙江痛下杀手。先后暂停浙江乡试、派亲信李卫出任浙江总督,设立风俗使衙门也是一项重要的部署。后来这一衙门先后在福建、广东设立,这一次轮到了湖南。
曾静、张熙的罪状是“谋反、叛逆及大不敬”,雍正的处理却是免罪释放后派他们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对这一史无前例、明显违反常规的做法,诸王及大臣两次上疏劝阻,但雍正不为所动。
他解释了三点理由。一是因为曾静案,他才发现允禩集团制造的流言,因而得以向天下臣民说明事实真相,并揭露允禩等人的罪恶;二是曾静只是误听、误信,受允禩集团余党和吕留良的欺骗。三是曾静能够在他感召下豁然醒悟,使天下臣民知道天下无不可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实现灵魂深处闹革命。
当然这三点只能说是似是而非的理由。他的真正目的是在随后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中,曾静可以作为反面教员为其所用。
但对吕留良案,雍正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弟子严鸿逵已死,被戮尸枭示。吕毅中斩决。其孙辈、妇孺发遣宁古塔为奴。所有的著作焚毁,为吕留良建祠、刻书的一干人也受到牵连。这是清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文字案。
曾静出狱前,对自己被指定的光荣任务十二万分的拥护,说皇恩浩荡,不敢言报。只要自己能到达的地方,逢人便宣扬皇上的圣德和本朝得天下的天经地义,以洗刷自己以前的罪恶。随即,以副部级干部杭奕禄为团长,以曾静为主角的大义觉迷宣讲团,从南京、苏州至杭州一路南下宣讲。
体贴入微的雍正还吩咐杭奕禄,到杭州后派专人送曾静至湖南巡抚衙门,让他先回家料理家务,再自行到观风整俗使衙门效力。从行程来看,江浙一带是曾静宣讲的重点。
曾静扬言,腹诽朝政的知识分子快些改弦更张,否则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等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狂热的反清分子,早已变身为反抽对手的一根鞭子。
整风
就这样,以曾静案为发韧,通过上谕、《大义觉迷录》、观风俗使衙门、官方宣讲团、从严处理吕留良案等一系列部署为抓手,雍正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国整风运动。雍正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
《雍正帝读书像》轴,清代宫廷画家绘。
第一个问题是清除矫诏得位流言的恶劣影响。
这个问题是雍正获得一系列坏名声的核心。这股流言自雍正继位之日起就开始传播,雍正也心知肚明。一方面除了宣称自己从来无意于皇位,心中叫苦不迭外,另一方面加快了对政敌的清算。随着允禩、允禟集团和年羹尧、隆科多的覆灭,流言源头被根除,以及几年煞费苦心的安排,雍正满以为此事已逐步平息。但通过曾静案才发现,之前的努力都是白费。
整风运动开始后,雍正直接针对曾静关于皇位问题的指责进行正面反击,逐条进行辩驳,即使泄露宫廷机密,也在所不惜。同时,严查散播流言的允禩等人的亲信,彻底清除允禩集团政治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树立满清夺取政权的合法性。
曾静反清的理论根据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对于满清借李自成覆灭明朝的机会夺取政权,曾静痛心首地说这是强盗劫去家财,又将主人赶出门外,占据我家。
对此,雍正坦率地承认“夷狄”的称谓,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照样成为圣君。以德治国是具备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第一标准。只要施仁政,得民心,就可做皇帝,而不论地域或民族。
对清朝入关得天下,雍正认为明朝亡于李自成之手,与满清毫无关系。当时吴三桂请求除寇安乱,所以才兴师平定,还安葬了崇祯帝,为明朝报怨雪耻。清朝得天下,比起汤、武通过武力覆灭前朝更为名正言顺。况且,大清建国80余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三个问题是威慑士绅集团,形成改革合力。
当时绝大多数士人热衷科举,他们对吕留良选评的时文感兴趣,对文中华夷之别等暗示反应不大。但抓住曾静反清这个特例严惩吕留良一案,主要目的是威慑士绅集团。
吕留良案判决于年(雍正八年),正式执行一直拖到年末。之所以拖这么久,是因为雍正要求全国“读书生监”就此案判决表态,直到各省都收到表示同意的“结状”后,判决才开始执行。
士绅是地方实力派,享有各种特权。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交结官府,甚至可以挟持、对抗官府。他们以其权势、文化及广泛的交游,成为议论朝政和地方事务,或品评人物等社会舆论的主要制造者。
康熙晚年,执政过宽,流弊重生,社会矛盾激化。导致雍正即位时接手了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雍正推行改革势必要侵占一部分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阻力重重。他的办法是集权,通过设立军机处更有效地控制官僚集团,得以比较顺利地推行澄清吏治,制止贪污,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政策。这当中,对于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士绅集团,无法直接纳入管制,但通过曾静案进行威慑,营造支持改革的氛围和合力,应该是题中之义。
余波
雍正死后才数月,他那“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谕旨早已被乾隆抛之脑后,不仅曾静、张熙马上被处死,《大义觉迷录》也被列入禁书销毁。
因为雍正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
现在雍正为了自己的目的,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一清二楚了。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说服力有限,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大家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捕风捉影,发挥想像。
雍正在这方面的失误,还由于皇权的极度加强导致自信心膨胀。他的愿望、独特的作风等,就可以通过他所掌握的庞大权力,基本不受干扰而发挥作用,终因过分违反封建统治常规,造成了不利影响。
这情形极像年“9·13”事件后,林副统帅葬身大漠,不顾下属的劝阻,向全党公开了林彪集团的反党纲领性文件“工程纪要”。当时毛的本意,一是要给林定罪,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行;二是他自信以自己的威望,群众看到那些反党罪证后,肯定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没想到却事与愿违。
陈丹青曾经在文章中回忆,知青们第一次公开学习“工程纪要”后,一阵沉默。散会时一位与他交好的知青大声地对他说,林秃子真正狼子野心,竟敢说伟大领袖是“绞肉机”,两人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一切尽在不言中。(网易)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